本文原载于台湾《十方》杂志一九九三年八月出刊十一卷 第十一期,作者秦明,系秦敏初女士笔名 ,1928.4.18日生于乐山五通桥,毕业于财贸干部学校,曾从事民族贸易工作,2001年11月22日离世,享年73岁。南怀瑾先生曾为其撰挽联:
为国为家情深,
一生宽厚载德。
横批:云来云去
(錄自一九九三年八月出刊《十方雜誌》第十一卷 第十一期)
懷師 五十年來的近事 秦 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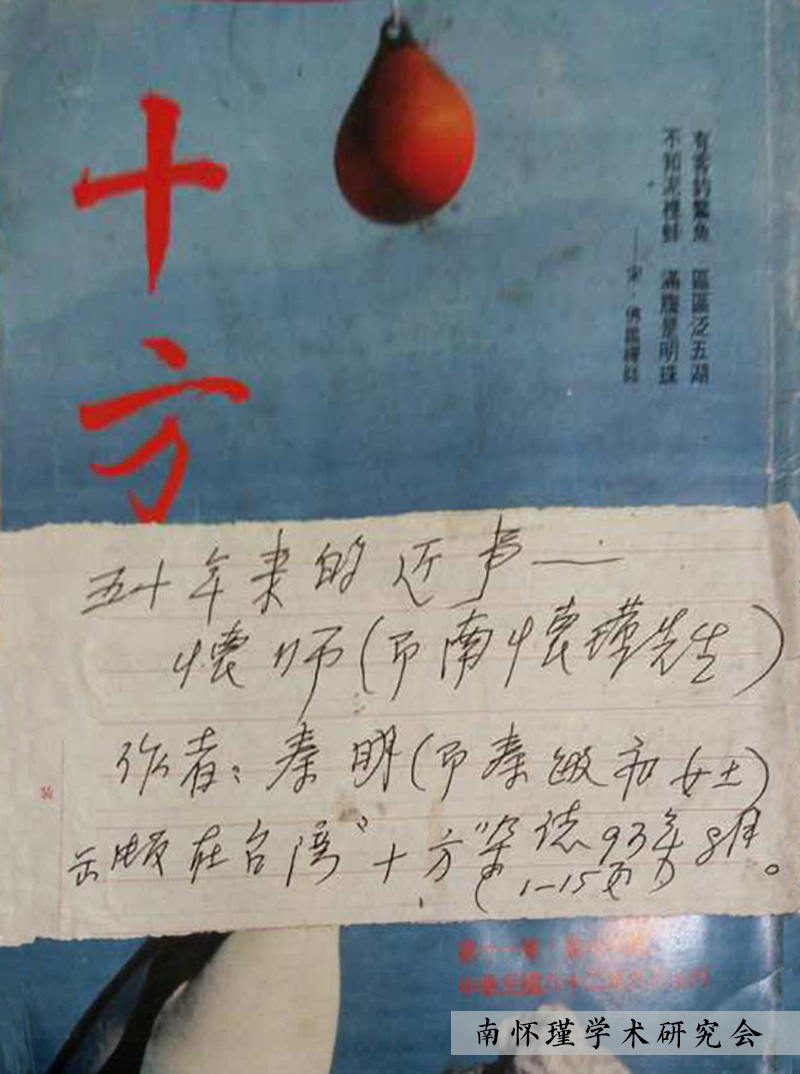

前塵非夢
半百光陰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從一個童年故事到兩鬢星霜來講,真有前塵如夢的感慨。但是這個夢境畢竟還是真實故事,它永恆的存在,永遠不會消失。說它奇特卻很平凡,說是平凡似乎又很奇特,如果不是這樣一個層風疊浪,驚險離奇的歷史大時代中,很可能不會使人永遠回憶,也不會使人永難期望將來的境界。
當我童年就讀中學的時代,那個時期的年號叫做民國三十四年,也就是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暑假我回到嘉定竹根灘五通橋外公家裡看望我的媽媽。現在我已無法回憶那年的暑假媽媽為什麼回五通橋。媽媽如果還活著,已是九十五歲人了。她當時也算是四川青年女性中的一位傑出人物,從師範畢業後,曾經擔任過隆昌的教育局長。在那個時代,女性出任教育行政首長的她還稱是絕無僅有的一位,所以很受人注目。她的學養是從我外公處得來,有很好的中文傳統文化的底子,又懂得中醫,對我來講媽媽亦母亦師。現在我要記述這個夢中的主角,一個崇高使人敬仰的人物,就是媽媽當年的老師南懷瑾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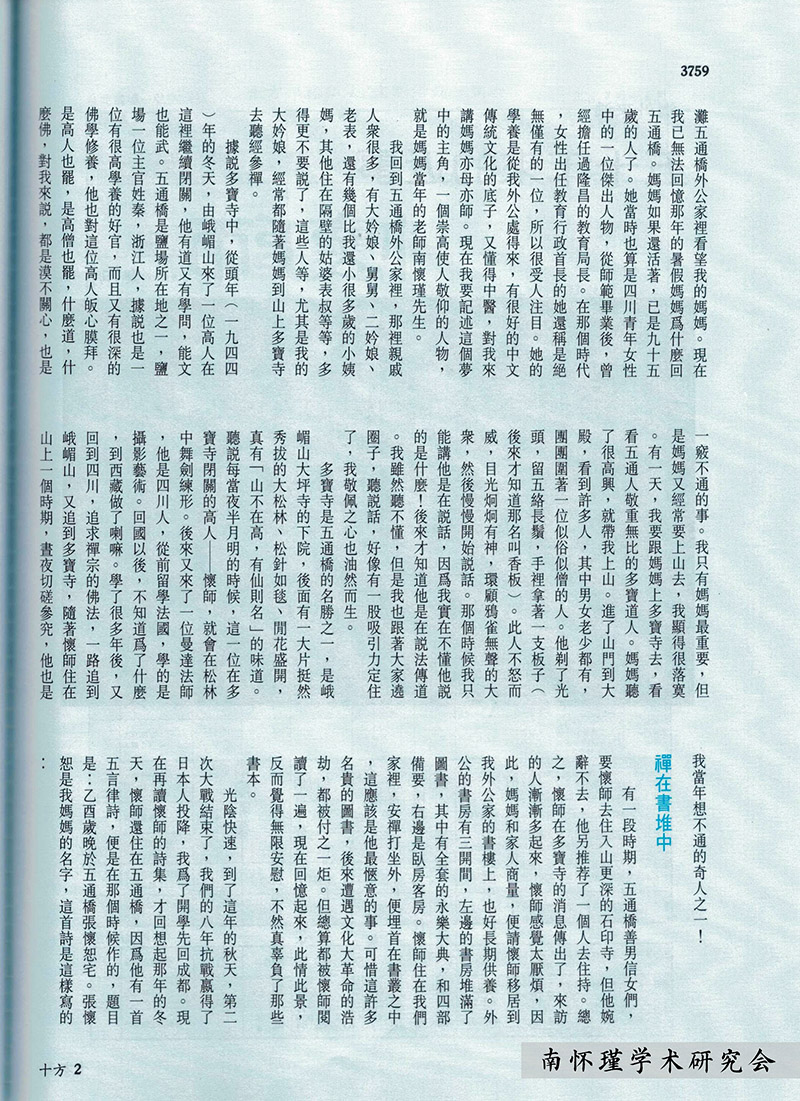
我回到五通橋外公家裡,那裡親戚人眾很多,有大妗娘、舅舅、二妗娘、老表,還有幾個比我還小很多歲的小姨媽,其他住在隔壁的姑婆表叔等等,多得更不要說了,這些人等,尤其是我的大妗娘,經常都隨著媽媽到山上多寶寺去聽經參禪。
據說多寶寺中,從頭年(一九四四)年的冬天,由峨嵋山來了一位高人在這裡繼續閉關,他有道又有學問,能文也能武。五通橋是鹽場所在地之一,鹽場一位主官姓秦,浙江人,據說也是一位有很高學養的好官,而且又有很深的佛學修養,他也對這位高人皈心膜拜。是高人也罷,是高僧也罷,什麼道,什麼佛,對我來說,都是漠不關心,也是一竅不通的事。我只有媽媽最重要,但是媽媽又經常要上山去,我顯得很落寞。有一天,我要跟媽媽上多寶寺去,看看五通人敬重無比的多寶道人。媽媽聽了很高興,就帶我上山。進了山門到大殿,看到許多人,其中男女老少都有,團團圍著一位似俗似僧的人。他剃了光頭,留五絡長鬚,手裡拿著一支板子(後來才知道那名叫香板)。此人不怒而威,目光炯炯有神,環顧鴉雀無聲的大眾,然後慢慢開始說話。那個時候我只能講他是在說話,因為我實在不懂他說的是什麼!後來才知道他是在說法傳道。我雖然聽不懂,但是我也跟著大家遶圈子,聽說話,好像有一股吸引力定住了,我敬佩之心也油然而生。
多寶寺是五通橋的名勝之一,是峨嵋山大坪寺的下院,後面有一大片挺然秀拔的大松林、松針如毯、閒花盛開,真有「山不在高,有仙則名」的味道。聽說每當夜半月明的時候,這一位在多寶寺閉關的高人 — 懷師,就會在松林中舞劍練形。後來又來了一位曼達法師,他是四川人,從前留學法國,學的是攝影藝術。回國以後,不知道為了什麼,到西藏做了喇嘛。學了很多年後,又回到四川,追求禪宗的佛法,一路追到峨嵋山,又追到多寶寺,隨著懷師住在山上一個時期,晝夜切磋參究,他也是我當年想不通的奇人之一!
禪在書堆中
有一段時期,五通橋善男信女們,要懷師去住入山更深的石印寺,但他婉辭不去,他另推荐了一個人去住持。總之,懷師在多寶寺的消息傳出了,來訪的人漸漸多起來,懷師感覺太厭煩,因此,媽媽和家人商量,便請懷師移居到我外公家的書樓上,也好長期供養。外公的書房有三開間,左邊的書房堆滿了圖書,其中有全套的永樂大典,和四部備要,右邊是臥房客房。懷師住在我們家裡,安禪打坐外,便埋首在書叢之中,這應該是他最愜意的事。可惜這許多名貴的圖書,後來遭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都被付之一炬。但總算都被懷師閱讀了一遍,現在回憶起來,此情此景,反而覺得無限安慰,不然真辜負了那些書本。
光陰快速,到了這年的秋天,第二次大戰結束了,我們的八年抗戰贏得了日本人投降,我為了開學先回成都。現在再讀懷師的詩集,才回想起那年的冬天,懷師還住在五通橋,因為他有一首五言律詩,便是在那個時候作的,題目是:乙酉歲晚於五通橋張懷恕宅。張懷恕是我媽媽的名字,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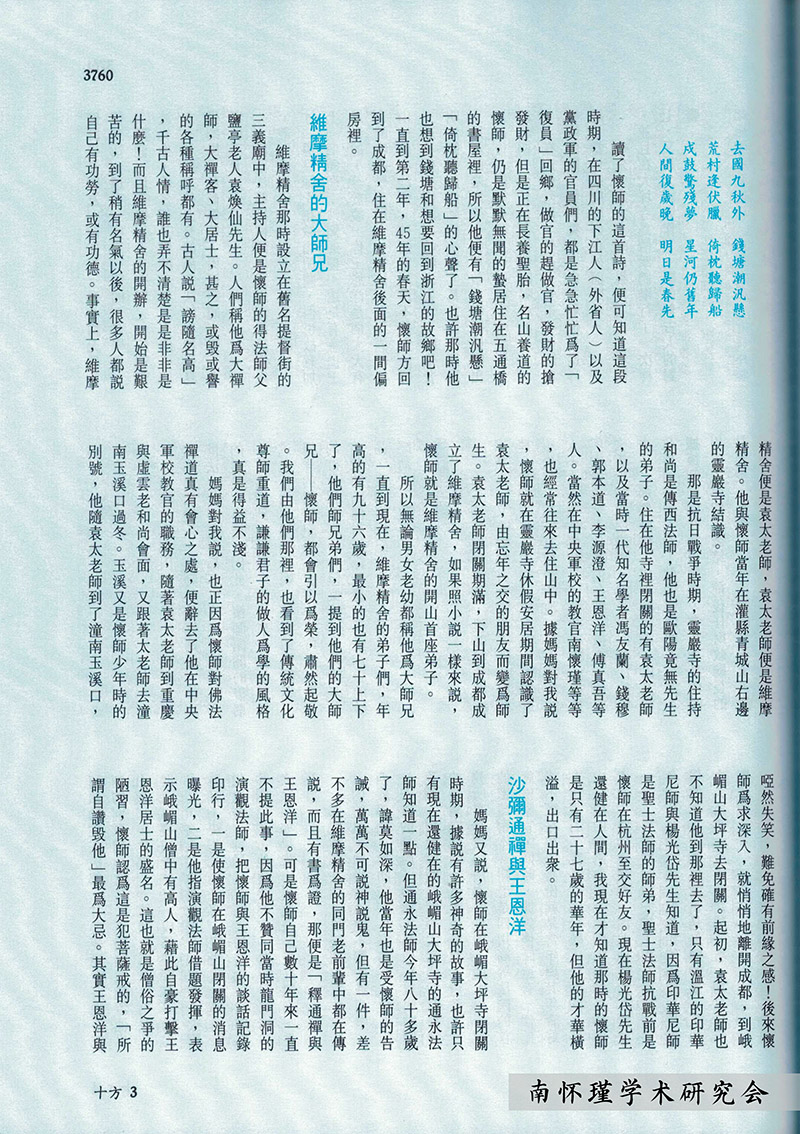
去國九秋外 錢塘潮汎懸
荒村逢伏臘 倚枕聽歸船
戍鼓驚殘夢 星河仍舊年
人間復歲晚 明日是春先
讀了懷師的這首詩,便可知道這段時期,在四川的下江人(外省人)以及黨政軍的官員們,都是急急忙忙為了「復員」回鄉,做官的趕做官,發財的搶發財,但是正在長養聖胎,名山養道的懷師,仍是默默無聞的蟄居住在五通橋的書屋裡,所以他便有「錢塘潮汎懸」「倚枕聽歸船」的心聲了。也許那時他也想到錢塘和想要回到浙江的故鄉吧!一直到第二年,45年的春天,懷師方回到了成都,住在維摩精舍後面的一間偏房裡。
維摩精舍的大師兄
維摩精舍那時設立在舊名提督街的三義廟中,主持人便是懷師的得法師父鹽亭老人袁煥仙先生。人們稱他為大禪師,大禪客、大居士,甚之,或毀或譽的各種稱呼都有。古人說「謗隨名高」,千古人情,誰也弄不清楚是是非非是什麼!而且維摩精舍的開辦,開始是艱苦的,到了稍有名氣以後,很多人都說自己有功勞,或有功德。事實上,維摩精舍便是袁太老師,袁太老師便是維摩精舍。他與懷師當年在灌縣青城山右邊的靈巖寺結識。
那是抗日戰爭時期,靈巖寺的住持和尚是傳西法師,他也是歐陽竟無先生的弟子。住在他寺裡閉關的有袁太老師,以及當時一代知名學者馮友蘭、錢穆、郭本道、李源澄、王恩洋、傅真吾等人。當然在中央軍校的教官南懷瑾等等,也經常往來去住山中。據媽媽對我說,懷師就在靈巖寺休假安居期間認識了袁太老師,由忘年之交的朋友而變為師生。袁太老師閉關期滿,下山到成都成立了維摩精舍,如果照小說一樣來說,懷師就是維摩精舍的開山首座弟子。
所以無論男女老幼都稱他為大師兄,一直到現在,維摩精舍的弟子們,年高的有九十六歲,最小的也有七十上下了,他們師兄弟們,一提到他們的大師兄 — 懷師,都會引以為榮,肅然起敬。我們由他們那裡,也看到了傳統文化尊師重道,謙謙君子的做人為學的風格,真是得益不淺。
媽媽對我說,也正因為懷師對佛法禪道真有會心之處,便辭去了他在中央軍校教官的職務,隨著袁太老師到重慶與虛雲老和尚會面,又跟著太老師去潼南玉溪口過冬。玉溪又是懷師少年時的別號,他隨袁太老師到了潼南玉溪口,啞然失笑,難免確有前緣之感!後來懷師為求深入,就悄悄地離開成都,到峨嵋山大坪寺去閉關。起初,袁太老師也不知道他到那裡去了,只有溫江的印華尼師與楊光岱先生知道,因為印華尼師是聖士法師的師弟,聖士法師抗戰前是懷師在杭州至交好友。現在楊光岱先生還健在人間,我現在才知道那時的懷師是只有二十七歲的華年,但他的才華橫溢,開口出眾。
沙彌通禪與王恩洋
媽媽又說,懷師在峨嵋大坪寺閉關時期,據說有許多神奇的故事,也許只有現在還健在的峨嵋山大坪寺的通永法師知道一點。但通永法師今年八十多歲了,諱莫如深,他當年也是受懷師的告誡,萬萬不可說神說鬼,但有一件,差不多在維摩精舍的同門老前輩中都在傳說,而且有書為證,那便是「釋通禪與王恩洋」。可是懷師自己數十年來一直不提此事,因為他不贊同當時龍門洞的演觀法師,把懷師與王恩洋的談話記錄印行,一是使懷師在峨嵋山閉關的消息曝光,二是他指演觀法師借題發揮,表示峨嵋山僧中有高人,藉此自豪打擊王恩洋居士的盛名。這也就是僧俗之爭的陋習,懷師認為這是犯菩薩戒的,「所謂自讚毀他」最為大忌。其實王恩洋與懷師也是朋友,例如馬一浮、謝無量、傅養恬,還有一些老一輩的知名學者、大師們,以及四川五老七賢之一的劉豫波先生,許多都是懷師忘年之交的好朋友。至於方外之交的滿空法師,神通具備的風了和尚等等,與懷師的交情,大家就不大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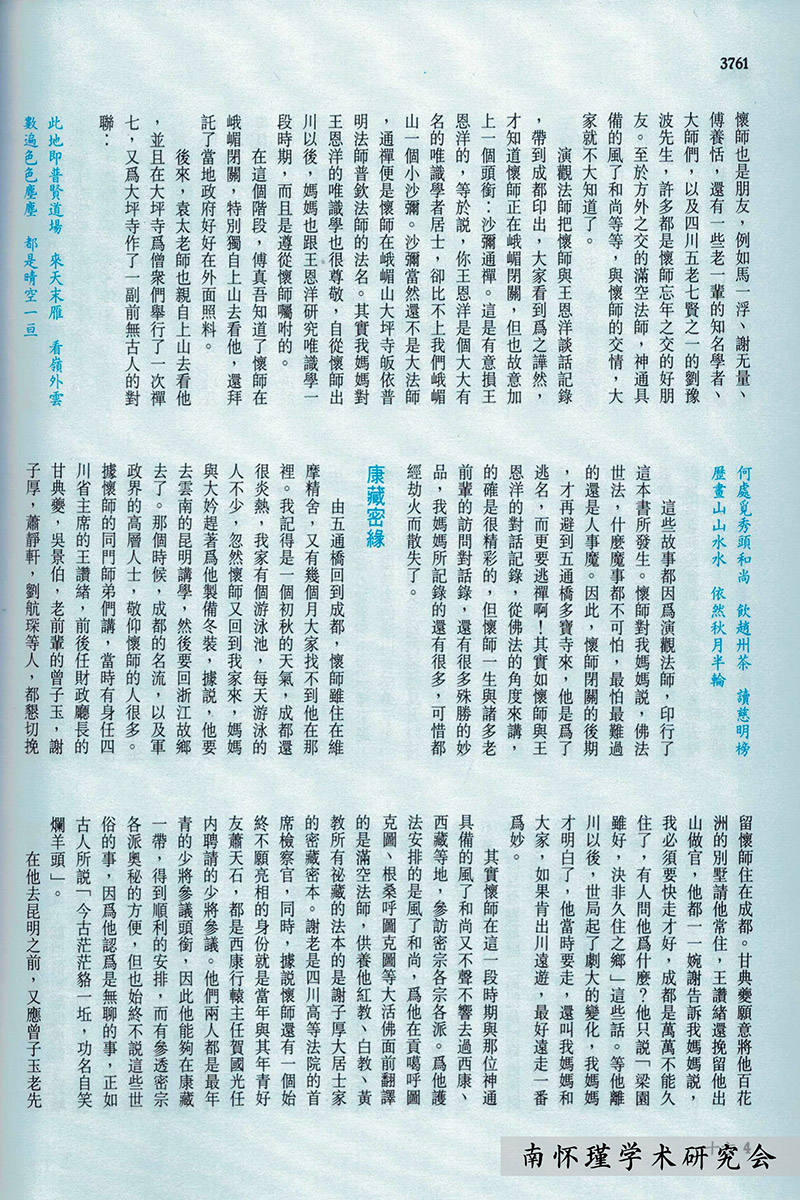
演觀法師把懷師與王恩洋談話記錄,帶到成都印出,大家看到為之譁然,才知道懷師正在峨嵋閉關,但也故意加上一個頭銜:沙彌通禪。這是有意損王恩洋的,等於說,你王恩洋是個大大有名的唯識學者居士,卻比不上我們峨嵋山一個小沙彌。沙彌當然還不是大法師,通禪便是懷師在峨嵋山大坪寺皈依普明法師普欽法師的法名。其實我媽媽對王恩洋的唯識學也很尊敬,自從懷師出川以後,媽媽也跟王恩洋研究唯識學一段時期,而且是遵從懷師囑咐的。
在這個階段,傅真吾知道了懷師在峨嵋閉關,特別獨自上山去看他,還拜託了當地政府好好在外面照料。
後來,袁太老師也親自上山去看他,并且在大坪寺為僧眾們舉行了一次禪七,又為大坪寺作了一副前無古人的對聯:
此地即普賢道場 來天末雁 看嶺外雲 數遍色色塵塵
都是晴空一亙
何處覓秀頭和尚 飲趙州茶 讀慈明榜 歷盡山山水水
依然秋月半輪
這些故事都因為演觀法師,印行了這本書所發生。懷師對我媽媽說,佛法世法,什麼魔事都不可怕,最怕最難過的還是人事魔。因此,懷師閉關的後期,才再避到五通橋多寶寺來,他是為了逃名,而更要逃禪啊!其實如懷師與王恩洋的對話記錄,從佛法的角度來講,的確是很精彩的,但懷師一生與諸多老前輩的訪問對話錄,還有根多殊勝的妙品,我媽媽所記錄的還有很多,可惜都經劫火而散失了。
康藏密緣
由五通橋回到成都,懷師雖住在維摩精舍,又有幾個月大家找不到他在那裡。我記得是一個初秋的天氣,成都還很炎熱,我家有個游泳池,每天游泳的人不少,忽然懷師又回到我家來,媽媽與大妗趕著為他製備冬裝,據說,他要去雲南的昆明講學,然後要回浙江故鄉去了。那個時候,成都的名流,以及軍政界的高層人士,敬仰懷師的人很多。據懷師的同門師弟們講,當時有身任四川省主席的王讚緒,前後任財政廳長的甘典夔﹑吳景伯,老前輩的曾子玉﹑謝子厚﹑蕭靜軒﹑劉航琛等人,都懇切挽留懷師住在成都。甘典夔願意將他百花洲的別墅請他常住,王讚緒還挽留他出山做官,他都一一婉謝告訴我媽媽說,我必須要快走才好,成都是萬萬不能久住了,有人問他為什麼?他只說「梁園雖好,決非久住之鄉」這些話。等他離川以後,世局起了劇大的變化,我媽媽才明白了,他當時要走,還叫我媽媽和大家,如果肯出川遠遊,最好遠走一番為妙。
其實懷師在這一段時期與那位神通具備的風了和尚又不聲不響去過西康、西藏等地,參訪密宗各宗各派。為他護法安排的是風了和尚,為他在貢噶呼圖克圖、根桑呼圖克圖等大活佛面前翻譯的是滿空法師,供養他紅教、白教、黃教所有祕藏的法本的是謝子厚大居士家的密藏密本。謝老是四川高等法院的首席檢察官,同時,據說懷師還有一個始終不願亮相的身份就是當年與其年輕好友蕭天石,都是西康行轅主任賀國光任內聘請的少將參議。他們兩人都是最年輕的少將參議頭銜,因此他能夠在康藏一帶,得到順利的安排,而有參透密宗各派奧秘的方便,但也始終不說這些世俗的事,因為他認為是無聊的事,正如古人所說「今古茫茫貉一坵,功名自笑爛羊頭」。

在他去昆明之前,又應曾子玉老先生的邀請到過大竹,去過明末清初鼎鼎大名的禪宗大師破山海明禪師的雙桂堂等地,講學弘法。這個時候,現還健在的辛亥老人,現年九十八歲黃埔畢業的名將傅淵希,那時還在達縣任警備司令。所以懷師在大竹的一些故事,傅老到今一提起來,還很得意。他們誼屬同門,過了半個世紀,路隔幾千里,友道情懷,老而彌篤。每逢年節,我們代表懷師去向傅老致敬或拜年,那便是他最開心的時候。喜笑顏開的讚嘆懷師的往事,以及懷師的學問修養,並感謝他,身在海外,依然隨時不忘故人的念舊高誼。
由大竹再回到成都,西藏的著名學者活佛貢噶呼圖克圖正率領一班高徒喇嘛,到了成都,他與懷師因緣特別投契,就在成都的古剎大慈寺,也就是唐代玄奘法師出國以前掛褡的寺院,貢噶活佛特別為懷師傳授了顯密大小戒律。貢噶活佛還親手書寫了藏文傳法傳戒的證書付給懷師,在懷師出川的時候,放在我家,媽媽代為保管,可惜這件珍貴希有的文件,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劫失去了。
出川的疑情
人生的聚散離合真是緣會無常,正如懷師詩集中的詞句:
雲水萍飄豈偶然 九年足跡遍西川
管他鬢到秋邊白 落得人間月似煙
腸空轉 事難全 又人間浮欲界天
樽前酒醒荒唐夢 君向潼南我向滇
懷師真要走了,他的老朋友中,最捨不得的一個是傅真吾。他名傅常,原是川軍劉湘的參謀長,後來是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參謀長,學禪又學密,說是與懷師切磋受益狠大。另有一個是伍心言,也是川中的名士,相傳是歐陽修後身,據說此人還擔任過劉湘的秘書長,他很欽佩懷師,曾經在懷師出川之前,親自趕到重慶送行,在北碚溫泉暢敘一晝夜,依依惜別。據說伍老先生不但記得三生的事,而且,還有些宿命通,他曾預言,蔣介石先生不會成功,不可能統一中國。當時我真不能想像,為什麼那麼多年歲地位都是老前輩的人,都低首甘心崇敬一個二三十歲的少年,豈不奇怪。
據懷師同門師弟說,當時有個中江人當過師長的林梅坡,認為懷師係一代奇才,他們認為只有南先生能挽當時政局之狂瀾。但是懷師從來視功名如糞土,亂世功名更不會為其所取。我媽媽認為他志在發掘、並要發揚光大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禪宗。那時懷師決心出川回鄉,便有人懷疑懷師與他的得法老師,袁太老師有了距離;因為那個時候,袁太老師出任第一屆國民大會的制憲國大代表,要去南京,他要懷師同行去南京。懷師是浙江人,在中央軍校任過教官,與蔣介石認識,同時懷師與陳誠又是家鄉的同門同學,袁太老師認為宏揚傳統文化與禪宗,懷師如果同去南京,得到當局的同意,便對佛法有所做為。但懷師認為,此時此世,佛也無能為力,認為如果為了傳統文化與佛法應特立獨行,從事社會工作,與其依賴權力,不如廣結社會群眾的善緣。所以懷師後來仍去昆明講學,在這點上引起少數人的議論,但老前輩們都知道懷師與袁太老師之間彼此一貫配合默契。這些故事都是我媽媽在平常閒談中,無意的向我提過一些,誰知事隔數十年,才證明他們師生之間,真是神奇默契。
袁太老師在南京參加制憲國大會議時,曾去過臺灣,在台北的龍山寺講過佛法,而結果呢!懷師從一九四九年起,便在臺灣一住三十六年,養道蓬萊,弘法東土,誰又能知他們師生之間的度世心情,是如何的呢!我的認為是偉大。現在懷師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影響,他的聲譽幾乎已遍及全球,袁太老師在靈山會上,一定也會為之拈花微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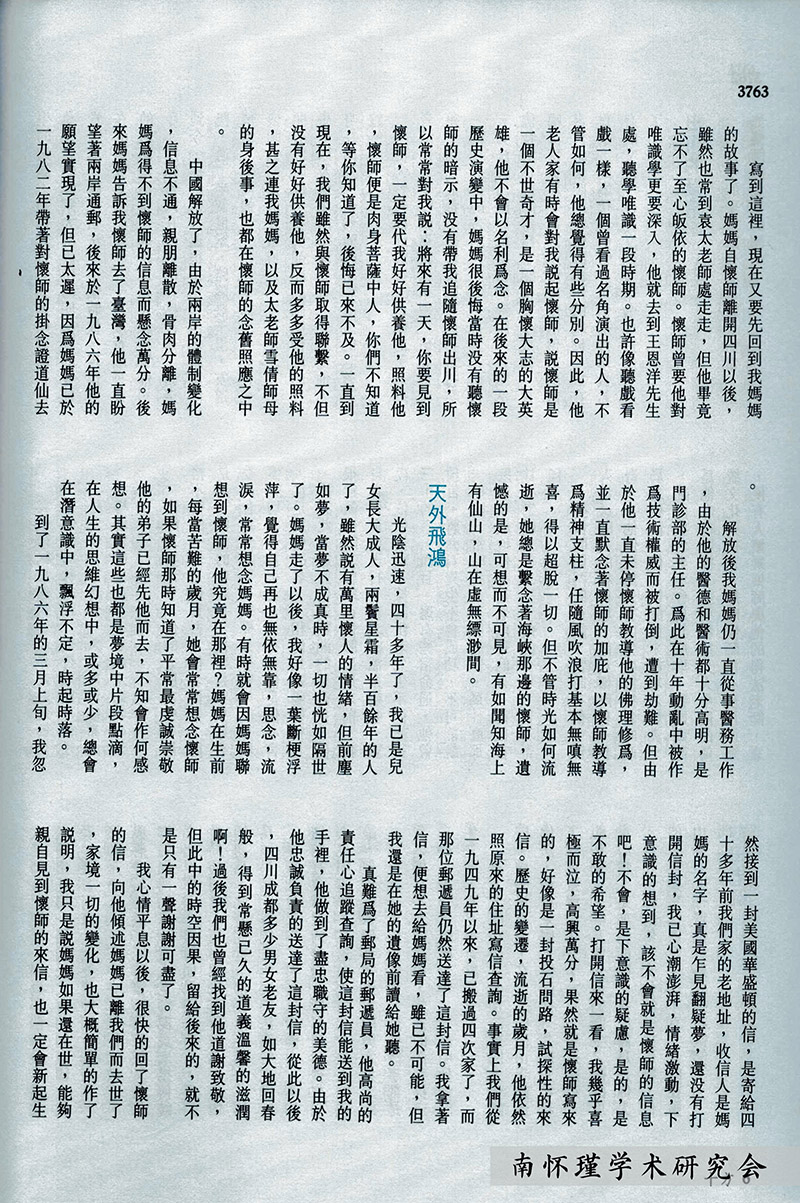
慈母老師
寫到這裡,現在又要先回到我媽媽的故事了。媽媽自懷師離開四川以後,雖然也常到袁太老師處走走,但他畢竟忘不了至心皈依的懷師。懷師曾要他對唯識學更要深入,他就去到王恩洋先生處,聽學唯識一段時期。也許像聽戲看戲一樣,一個曾看過名角演出的人,不管如何,他總覺得有些分別。因此,他老人家有時會對我說起懷師,說懷師是一個不世奇才,是一個胸懷大志的大英雄,他不會以名利為念。在後來的一段歷史演變中,媽媽很後悔當時沒有聽懷師的暗示,沒有帶我追隨懷師出川,所以常常對我說:將來有一天,你要見到懷師,一定要代我好好供養他,照料他,懷師便是肉身菩薩中人,你們不知道,等你知道了,後悔已來不及。一直到現在,我們雖然與懷師取得聯繫,不但沒有好好供養他,反而多多受他的照料,甚之連我媽媽,以及太老師雪倩師母的身後事,也都在懷師的念舊照應之中。
中國解放了,由於兩岸的體制變化,信息不通,親朋離散,骨肉分離,媽媽為得不到懷師的信息而懸念萬分。後來媽媽告訴我懷師去了臺灣,他一直盼望著兩岸通郵,後來於一九八六年他的願望實現了,但已太遲,因為媽媽已於一九八二年帶著對懷師的掛念證道仙去。
解放後我媽媽仍一直從事醫務工作,由於他的醫德和醫術都十分高明,是門診部的主任。為此在十年動亂中被作為技術權威而被打倒,遭到劫難。但由於他一直未停懷師教導他的佛理修為,並一直默念著懷師的加庇,以懷師教導為精神支柱,任隨風吹浪打基本無嗔無喜,得以超脫一切。但不管時光如何流逝,她總是繫念著海峽那邊的懷師,遺憾的是,可想而不可見,有如「聞知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渺間」。
天外飛鴻
光陰迅速,四十多年了,我已是兒女長大成人,兩鬢星霜,半百餘年的人了,雖然說有萬里懷人的情緒,但前塵如夢,當夢不成真時,一切也恍如隔世了。媽媽走了以後,我好像一葉斷梗浮萍,覺得自己再也無依無靠,思念,流淚,常常想念媽媽。有時就會因媽媽聯想到懷師,他究竟在那裡?媽媽在生前,每當苦難的歲月,她會常常想念懷師,如果懷師那時知道了平常最虔誠崇敬他的弟子已經先他而去,不知會作何感想。其實這些也都是夢境中片段點滴,在人生的思維幻想中,或多或少,總會在潛意識中,飄浮不定,時起時落。
到了一九八六年的三月上旬,我忽然接到一封美國華盛頓的信,是寄給四十多年前我們家的老地址,收信人是媽媽的名字,真是乍見翻疑夢,還沒有打開信封,我已心潮澎湃,情緒激動,下意識的想到,該不會就是懷師的信息吧!不會,是下意識的疑慮,是的,是不敢的希望。打開信來一看,我幾乎喜極而泣,高興萬分,果然就是懷師寫來的,好像是一封投石問路,試探性的來信。歷史的變遷,流逝的歲月,他依然照原來的住址寫信查詢。事實上我們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已搬過四次家了,而那位郵遞員仍然送達了這封信。我拿著信,便想去給媽媽看,雖已不可能,但我還是在她的遺像前讀給她聽。
真難為了郵局的郵遞員,他高尚的責任心追蹤查詢,使這封信能送到我的手裡,他做到了盡忠職守的美德。由於他忠誠負責的送達了這封信,從此以後,四川成都多少男女老友,如大地回春般,得到常懸已久的道義溫馨的滋潤啊!過後我們也曾經找到他道謝致敬,但此中的時空因果,留給後來的,就不是只有一聲謝謝可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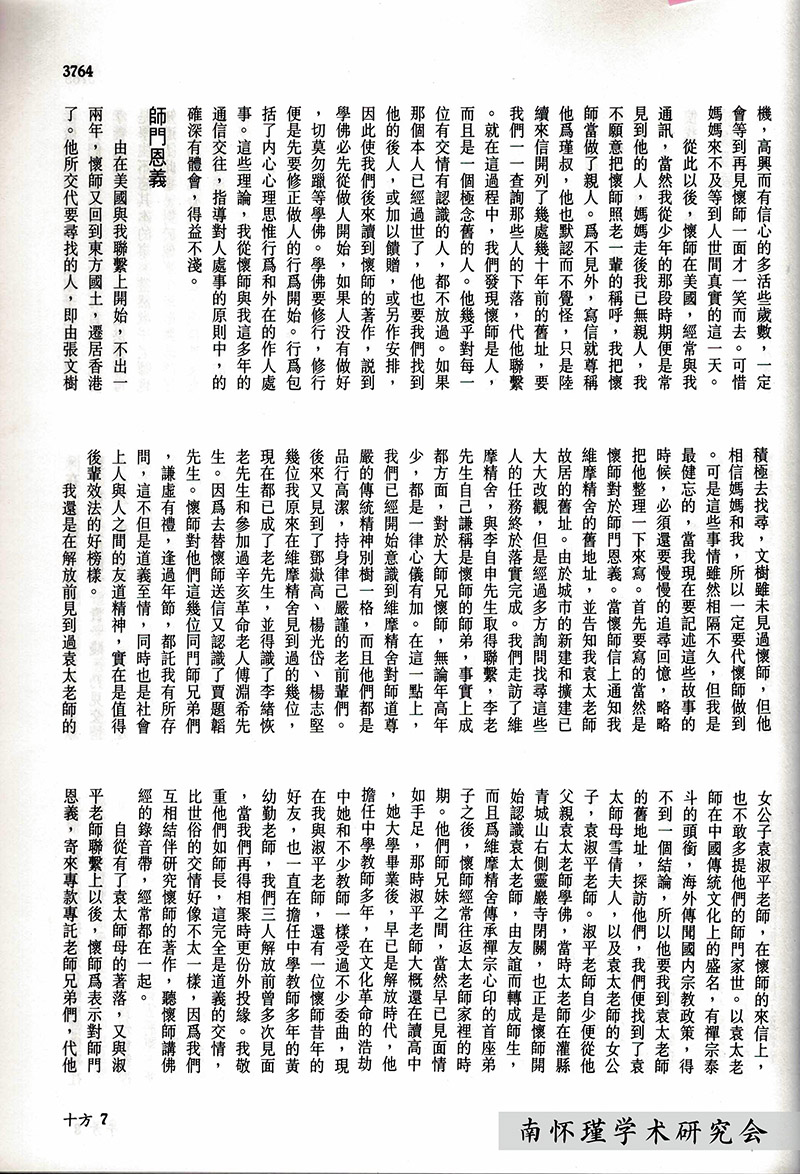
我心情平息以後,很快的回了懷師的信,向他傾述媽媽已離我們而去世了,家境一切的變化,也大概簡單的作了說明,我只是說媽媽如果還在世,能夠親自見到懷師的來信,也一定會新起生機,高興而有信心的多活些歲數,一定會等到再見懷師一面才一笑而去。可惜媽媽來不及等到人世間真實的這一天。
從此以後,懷師在美國,經常與我通訊,當然我從少年的那段時期便是常見到他的人,媽媽走後我已無親人,我不願意把懷師照老一輩的稱呼,我把懷師當做了親人。為不見外,寫信就尊稱他為瑾叔,他也默認而不覺怪,只是陸續來信開列了幾處幾十年前的舊址,要我們一一查詢那些人的下落,代他聯繫。就在這過程中,我們發現懷師是人,而且是一個極念舊的人。他幾乎對每一位有交情有認識的人,都不放過。如果那個本人已經過世了,他也要我們找到他的後人,或加以饋贈,或另作安排,因此使我們後來讀到懷師的著作,說到學佛必先從做人開始,如果人沒有做好,切莫勿躐等學佛。學佛要修行,修行便是先要修正做人的行為開始。行為包括了內心心理思惟行為和外在的作人處事。這些理論,我從懷師與我這多年的通信交往,指導對人處事的原則中,的確深有體會,得益不淺。
師門恩義
由在美國與我聯繫上開始,不出一兩年,懷師又回到東方國土,遷居香港了。他所交代要尋找的人,即由張文樹積極去找尋,文樹雖未見過懷師,但他相信媽媽和我,所以一定要代懷師做到。可是這些事情雖然相隔不久,但我是最健忘的,當我現在要記述這些故事的時候,必須還要慢慢的追尋回憶,略略把他整理一下來寫。首先要寫的當然是懷師對於師門恩義。當懷師信上通知我維摩精舍的舊地址,並告知我袁太老師故居的舊址。由於城市的新建和擴建已大大改觀,但是經過多方詢問找尋這些人的任務終於落實完成。我們走訪了維摩精舍,與李自申先生取得聯繫,李老先生自己謙稱是懷師的師弟,事實上成都方面,對於大師兄懷師,無論年高年少,都是一律心儀有加。在這一點上,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維摩精舍對師道尊嚴的傳統精神別樹一格,而且他們都是品行高潔,持身律己嚴謹的老前輩們。後來又見到了鄧嶽高、楊光岱、楊志堅幾位我原來在維摩精舍見到過的幾位,現在都已成了老先生,并得識了李緒恢老先生和參加過辛亥革命老人傅淵希先生。因為去替懷師送信又認識了賈題韜先生。懷師對他們這幾位同門師兄弟們,謙虛有禮,逢年過節,都託我有所存問,這不但是道義至情,同時也是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友道精神,實在是值得後輩效法的好榜樣。
我還是在解放前見到過袁太老師的女公子袁淑平老師,在懷師的來信上,也不敢多提他們的師門家世。以袁太老師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盛名,有禪宗泰斗的頭銜,海外傳聞國內宗教政策,得不到一個結論,所以他要我到袁太老師的舊地址,採訪他們,我們便找到了袁太師母雪倩夫人,以及袁太老師的女公子,袁淑平老師。淑平老師自少便從他父親袁太老師學佛,當時太老師在灌縣青城山右側靈巖寺閉關,也正是懷師開始認識袁太老師,由友誼而轉成師生,而且為維摩精舍傳承禪宗心印的首座弟子之後,懷師經常往返太老師家裡的時期。他們師兄妹之間,當然早已見面情如手足,那時淑平老師大概還在讀高中,她大學畢業後,早已是解放時代,她擔任中學教師多年,在文化革命的浩劫中她和不少教師一樣受過不少委曲,現在我與淑平老師,還有一位懷師昔年的好友,也一直在擔任中學教師多年的黃幼勤老師,我們三人解放前曾多次見面,當我們再得相聚時更份外投緣。我敬重他們如師長,這完全是道義的交情,比世俗的交情好像不太一樣,因為我們互相結伴研究懷師的著作,聽懷師講佛經的錄音帶,經常都在一起。
自從有了袁太師母的著落,又與淑平老師聯繫上以後,懷師為表示對師門恩義,寄來專款專託老師兄弟們,代他孝敬供養師母,而且怕淑平老師負累,要我們千萬不要使他心理有負擔;兒女孝養老母,是兒女的事,學生供養師母是學生不忘其本的事。當然淑平老師也知道了此事,對於她平生最敬佩的師兄之作為,此心也不必細表,她自然又直接與懷師通信聯絡,懷師素知師妹的個性學養,為人處事的種種,非常愛護師妹,因此淑平老師在佛法的修為上更突飛猛進,已經不是當年停滯在得少為足的階段上了。不過這些我到底還是外行,什麼見地與功夫都談不上,只是看來似乎有點高山仰止而已。到九一年三月份袁太師母逝世,經淑平老師與大家同意,將懷師存儲供養師母的專款也完全用在安葬師母身後事上,可以說他是心安理得了。但懷師留給我們做為做人處事的榜樣,卻不是有關資財與物資的形式,而是無限的情誼。不但如此,在這裡我還須說明,如懷師對於我母親幾度遷葬的事,也都是如此盡心盡力,關懷得很,因為土地環境的關係,遷葬太費神,懷師才寫信教我早應火化母親遺骸,他告訴我佛門的名言「一火能燒三世業」,我最後遵照懷師的囑咐辦了,才使我母親了卻無生。

前緣續夢
懷舊念舊是人之常情,但亦不盡然,在一般世俗凡塵中人,往往會喜新厭舊。如古人所說「一貴一賤,乃見交情。一死一生,交情乃見。」念舊不一定是平常的事,但以我的感想,懷師數十年來不但念舊情深,而且幾乎有無微不至的行誼,此正是大乘佛法菩薩學處菩提薩埵的行為。據佛法所講,菩提是覺悟,薩埵是有情,翻成中文簡化來說,菩薩便是悟道了的有情人。既然悟道,還未忘情,沒有忘情,怎樣悟道?此亦正是我們凡夫不了解的道理了。
在四川懷師最關心的當然是師門一段因緣,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的心目中,懷師便是四川人。凡是四川的道友們,從來不覺得他是下江人,外省人,所以在情感上特別的親切。但他在友道上還有三四個人,是與他抗戰初期入川之初交情深厚的人,有錢宗本、傳西法師、印華法師與黃幼勤四位,都是懷師到成都後最初交好的良友。尤其是錢宗本,單名一個吉字,所以也叫錢吉。他是彭縣人,有一段非常慘痛的戀愛故事;年青的時候,在封建思想極深厚的彭縣鄉下,他與同村的一個少女有了戀情,結果被女方家裡知道了,家族群起反對,他們想要離家出走。但那個少女卻被家族們抓回去,活埋了。錢宗本懷恨在心,便要殺人放火,結果受一高僧指點勸化,錢宗本就帶著老母離家,出家為僧,住在成都的貴州會館成都佛學社裡,養母修行。
懷師初到成都就寓居在貴州會館裡,因為會館供的神像是南霽雲將軍,所以懷師寄居在那裡,與錢宗本成為莫逆之交。不到半年,懷師要去川南雲貴邊境,擔任大小涼山墾植公司總經理,兼自衛團總指揮的職務。錢宗本奉母還俗,追隨懷師左右,到川滇邊境辛苦維護懷師。後來懷師回到成都,任職中央軍校,錢宗本也回到成都奉母安居,直到懷師學佛,又去了峨嵋山閉關,錢宗本方自謀生活,做小生意。好像也在這一段時間裡結婚成家,以後錢宗本與傳西法師、印華法師、黃幼勤都認識也成了好朋友。現在事隔數十年,經過多少風風雨雨的大小劫難,懷師找他不到,據說,懷師與黃幼勤取得聯絡以後,才由黃幼勤老師在信上告訴懷師,在文化大革命時期,還見過錢宗本一面,那時他在街上擺地攤賣舊衣服,還把一條很好的裙子,要送給黃老師,並且再三打聽懷師的下落。那種情形說來是小事,其實是多麼感人的故事啊!「當時只是尋常事,過後思量倍有情」確是一點也不錯的名言。
據說,錢宗本與懷師最初結識的時候,作了一首為老一輩子極為稱讚的詩贈懷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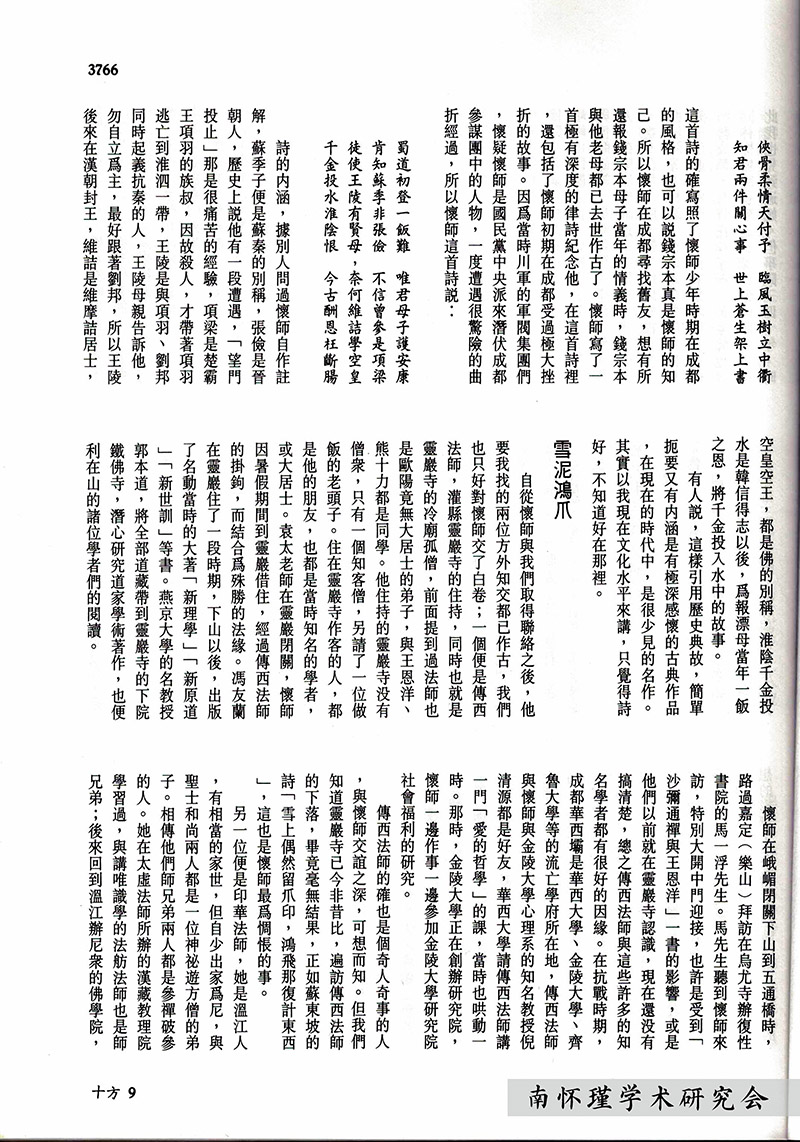
俠骨柔情天付予 臨風玉樹立中衢
知君兩件關心事 世上蒼生架上書
這首詩的確寫照了懷師少年時期在成都的風格,也可以說錢宗本真是懷師的知己。所以懷師在成都尋找舊友,想有所還報錢宗本母子當年的情義時,錢宗本與他老母都已去世作古了。懷師寫了一首極有深度的律詩紀念他,在這首詩裡,還包括了懷師初期在成都受過極大挫折的故事。因為當時川軍的軍閥集團們,懷疑懷師是國民黨中央派來潛伏成都參謀團中的人物,一度遭遇很驚險的曲折經過,所以懷師這首詩說:
蜀道初登一飯難 唯君母子護安康
肯知蘇季非張儉 不信曾參是項梁
徒使王陵有賢母 奈何維詰學空皇
千金投水淮陰恨 今古酬恩枉斷腸
詩的內涵,據別人問過懷師自作註解,蘇季子便是蘇秦的別稱,張儉是晉朝人,歷史上說他有一段遭遇,「望門投止」那是很痛苦的經驗,項梁是楚霸王項羽的族叔,因故殺人,才帶著項羽逃亡到淮泗一帶,王陵是與項羽、劉邦同時起義抗秦的人,王陵母親告訴他,勿自立為主,最好跟著劉邦,所以王陵後來在漢朝封王,維詰是維摩詰居士,空皇空王,都是佛的別稱,淮陰千金投水是韓信得志以後,為報漂母當年一飯之恩,將千金投入水中的故事。
有人說,這樣引用歷史典故,簡單扼要又有內涵是有極深感懷的古典作品,在現在的時代中,是很少見的名作。其實以我現在文化水平來講,只覺得詩好,不知道好在那裡。
雪泥鴻爪
自從懷師與我們取得聯絡之後,他要我找的兩位方外知交都已作古,我們也只好對懷師交了白卷;一個便是傳西法師,灌縣靈巖寺的住持,同時也就是靈巖寺的冷廟孤僧,前面提到過法師也是歐陽竟無大居士的弟子,與王恩洋、熊十力都是同學。他住持的靈巖寺沒有僧眾,只有一個知客僧,另請了一位做飯的老頭子。住在靈巖寺作客的人,都是他的朋友,也都是當時知名的學者,或大居士。袁太老師在靈巖閉關,懷師因暑假期間到靈巖借住,經過傳西法師的掛鉤,而結合為殊勝的法緣。馮友蘭在靈巖住了一段時期,下山以後,出版了名動當時的大著「新理學」「新原道」「新世訓」等書。燕京大學的名教授郭本道,將全部道藏帶到靈巖寺的下院鐵佛寺,潛心研究道家學術著作,也便利在山的諸位學者們的閱讀。
懷師在峨嵋閉關下山到五通橋時,路過嘉定(樂山)拜訪在烏尤寺辦復性書院的馬一浮先生。馬先生聽到懷師來訪,特別大開中門迎接,也許是受到「沙彌通禪與王恩洋」一書的影響,或是他們以前就在靈巖寺認識,現在還沒有搞清楚,總之傳西法師與這些許多的知名學者都有很好的因緣。在抗戰時期,成都華西壩是華西大學、金陵大學、齊魯大學等的流亡學府所在地,傳西法師與懷師與金陵大學心理系的知名教授倪清源都是好友,華西大學請傳西法師講一門「愛的哲學」的課,當時也哄動一時。那時,金陵大學正在創辦研究院,懷師一邊作事一邊參加金陵大學研究院社會福利的研究。
傳西法師的確也是個奇人奇事的人,與懷師交誼之深,可想而知。但我們知道靈巖寺已今非昔比,遍訪傳西法師的下落,畢竟毫無結果,正如蘇東坡的詩「雪上偶然留爪印,鴻飛那復計東西」,這也是懷師最為惆悵的事。

另一位便是印華法師,她是溫江人,有相當的家世,但自少出家為尼,與聖士和尚兩人都是一位神祕遊方僧的弟子。相傳他們師兄弟兩人都是參禪破參的人。她在太虛法師所辦的漢藏教理院學習過,與講唯識學的法舫法師也是師兄弟;後來回到溫江辦尼眾的佛學院,有學僧百人左右。她是當時川西尼眾中的翹楚,也是一位極有學養的人。有時也請懷師在佛學院講學授課,同時又向懷師請益。懷師在峨嵋閉關時期,她是虔誠發心供養的外護之一。
懷師要我們尋訪,結果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經歷劫而去了。懷師又要我們找到她俗家的侄子,加以存問,總算了卻懷師一番心願。我們在懷師的詩集中,看見一首憶印華法師的詩:
印心促膝記當年 定起繩床月滿天
幾點臘梅花欲蕊 經窗相對雨無言
人生的因緣際遇,幸與不幸,真如佛說的不可思議。遊於方之外的兩位法師無代懷師找到,交了白卷,可是一位在方之內的老朋友黃幼勤老師,總算經過一些轉折,最後找到了。黃老師比懷師小五歲,懷師在成都這個階段,上峨嵋山閉關之前,她剛考上朝陽大學就與懷師認識。那時朝陽大學流亡到大後方,在望江樓附近,與四川大學在一起,并不在華西壩一帶,所以她沒有與傳西法師等人相識,否則她在那個時候也許早已進入佛門了。後來懷師從五通橋回轉成都,有時在我家裡,黃老師也曾同林梅坡師長來過我家與懷師晤談,因此我也見到過她。但事隔三四十年,時代與社會的變化又那麼大,黃幼勤老師她們搬遷在那裡,尋尋覓覓結果,總算找到了她的住處,可是等我們拿著懷師的信去看她時,也正同她先生伉儷二兩人,整裝待發,第二天要動身去美國探望他女兒女婿。於是只匆匆交代了懷師的通訊地址給她,以後的事,就由她們自己在美國與懷師取得聯絡。過了一年多,她們伉儷從美國回來了,才有機會使我與袁淑平老師、黃幼勤老師三人變成忘輩份的道義莫逆之交。她們二位實在是我的良師益友,我們能定期隨著成都的老前輩們共同研究佛法,有懷師的錄音帶和著作,使我們大家的晚年,得到精神上的皈依,樂趣無窮。老實說我們在這幾年的平靜歲月中,悠遊自在,實在都是懷師之所賜,這可不是一句虛言的客氣話,有人還引用了陳摶老祖的一對聯語來形容懷師:「開張天岸馬,奇逸人中龍」。懷師就是龍,龍行一步,百草沾恩,希望他步步行願,還要普福群生。
松月和尚與大坪寺
峨嵋山在歷史上有數不清的多少神話傳說,也有若干高人逸士的蹤跡。懷師在四川與峨嵋、青城兩處仙佛名山,都有很深的因緣。尤其是中峰的大坪寺,是懷師三年閉關,專修與閱讀全部大藏經的勝地。我可以理解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峨嵋山在他心中是永遠不會忘情的。大坪寺的開山祖師是松月老和尚,這位高僧祖師的來歷也是永遠無法查考的。媽媽在生的時候說起過,她曾問過懷師松月和尚是什麼時候的人,懷師說應是明末避世的得道高人,出家以後,獨自住在中峰絕頂的榛莽叢中,的確只有茅草蓋頭,沒有吃的,只有吃烏頭;那是一種毒藥草,就是天雄、附子之類。沒有徒弟只有猴子、老鴉、蛇,三種生物與他為伍,還有一隻為他巡山的黑虎。也不知他幾時入山,幾時圓寂,到了康熙初年冬天,寺眾必會煮一天一夜的烏頭,全體常住眾都要吃,這是為了紀念松月祖師的草衣木食,專修苦行的精神。
據說,大坪寺中的蛇與猴子、老鴉都受過松月祖師的三皈五戒。歷代以來,大坪寺中的蛇,決不咬人,如果出了山門,人要惹它,那就不客氣了。那隻黑虎據說與懷師有很深的特別因緣,可惜是個什麼故事,媽媽沒有對我細說,我也忘記了問她。懷師選定這個地方閉關,據說是普欽大法師的提議,印華法師的介紹,因為大坪寺藏有全部大藏經。在那個時代,一個寺院能藏有全部大藏經的並不多,尤其是受帝王封建傳統思想的影響,大藏經不是隨便可以閱讀的。懷師是個在家居士,更無資格准許入山閉關閱藏,那是佛教的規矩。可是普欽大法師是負有盛名的大德,他是大坪寺嫡系出家的弟子,由他提議允許,又加上許多重要人物的關係,閉關有條件,要懷師在閉關閱經的三年時期,穿上僧衣,成為大坪寺正式的弟子。這就是後來演觀法師,要為峨嵋山上的和尚們出氣,央請懷師出場,煞一煞王恩洋大居士素來看不起出家人的傲氣,才有「沙彌通禪與王恩洋」對話錄的前因後果。

大坪寺在當時真是一個絕險的孤峰,只有兩條懸崖峭壁的山路,猴子坡與蛇倒退。由這兩個坡度的命名,就可知道真是不太好走的路,所以遊人香客并不多。山上無水,只有一個靠天落雨和冬季冰雪所化的蓄水池。到了秋末冬初,大約舊曆十月之後,便大雪封山,好幾個月寸步難行。我們在懷師的詩集中,讀到他的:
長憶峨嵋金頂路 萬山冰雪月臨扉
也就可以心嚮往之,想像得到的境界,那是多麼美麗,又多麼淒清的情景啊!
在這樣的孤峰頂上閉關真不容易,可是當懷師在大坪寺的時候,也帶來了大坪寺最興旺的道氣。那時通字輩的青年僧眾,一時之間,便出家了七八位,其中因懷師的關係而入山出家的不少,有大學生,有軍官,也有軍人出身的,所以當時峨嵋山的和尚們說,大坪寺最近出家的和尚有六通具足的傳聞。
修苦行,擔任執役僧,常常要下山挑米,買辦雜物的通字輩中人,使懷師最懷念不忘。其中經常為他補充日用品,還在早晚勞務之餘跟著修行的師兄弟中,便有啞吧師兄與通永法師。這也是懷師對我媽媽講過的苦行高僧中最出色的兩位。據說啞吧師兄聰明絕頂,懷師說他究竟會不會講話也不必深問。通永法師在懷師出川以後到過我家,訪問懷師的下落,對懷師的道義之情的確不比尋常。我們背後有人叫他扁擔和尚,因為他是挑米上山的執役僧,苦行僧,修行第一,人又好,大家都很喜歡他,尊敬他。他現在已八十多歲,比懷師年長。但他們二人誰是師兄,誰是師弟都分不清,他們彼此稱師兄。據說,他的俗家是貴州人,是老一輩的軍人出身,基本不識字,但在峨嵋山僧眾中,大多都知道他是開了智慧的和尚。所謂開了智慧,便是悟道了的意思。可是他自己不承認,自從大坪寺毀在文化大革命期中,寺院也沒有了,老少僧眾,死的死走的走,真是人境兩空了。通永法師無處可歸,便被他徒弟接去掛褡在萬年寺中。他徒弟是萬年寺主持,他在萬年寺中直到現在。
我們奉懷師的指示與通永法師取得聯絡之後,他是多麼的高興啊!他希望還要見到懷師,同時也希望懷師回來重建大坪寺。每次他來我家,或我們隨著維摩精舍的老前輩們上峨嵋山去看他,我總覺得他清淨光明的童心永遠常在。一提到懷師他就笑了,懷師交代我們,要好好的供養他,但他卻自己出錢,為懷師請了許多出家法師,在成都文殊院為懷師念經,做法事,祈求懷師長壽住世。我們還把他這場法會的錄音帶寄給了懷師,懷師回信要我們向他道謝,並且要我們告訴他,長壽是三災八難的一難,師兄啊!不要枉自多情吧!看來,他們二人都在打機鋒,說禪話,我們也只有奉命行事,不懂,就袖手旁聽吧!通永法師還經常對我們提出,要想到海外去看懷師。但我們和他的徒弟及其皈依弟子們都婉轉勸他,年事太高了,不宜遠行。
大坪寺通字輩的師兄弟中還有一位通孝法師,現在住在金頂白雲菴,他是青年便到西藏去學法的,與通永法師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但他對大坪寺的重建卻很懸念。據說曾經將一件偶然得到價值很高的法寶,交託專送到海外去給懷師,要他設法重修大坪寺,結果懷師又派專人還給他說,重建大坪寺是將來的因緣,法寶歸法寶,原璧歸趙。由此看來,通孝法師也是一位了不起的高人,他們都是心存大坪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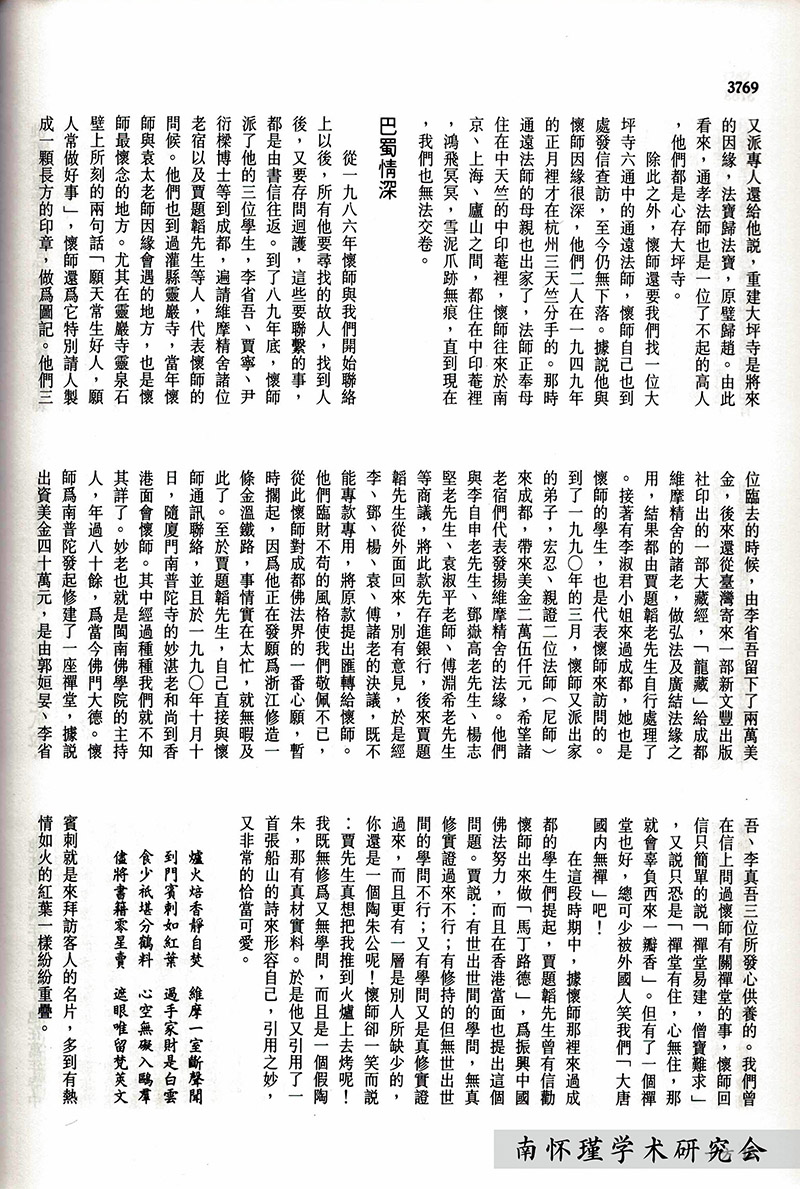
除此之外,懷師還要我們找一位大坪寺六通中的通遠法師,懷師自己也到處發信查訪,至今仍無下落。據說他與懷師因緣很深,他們二人在一九四九年的正月裡才在杭州三天竺分手的。那時通遠法師的母親也出家了,法師正奉母住在中天竺的中印菴裡,懷師往來於南京、上海、廬山之間,都往在中印菴裡,鴻飛冥冥,雪泥爪跡無痕,直到現在,我們也無法交卷。
巴蜀情深
從一九八六年懷師與我們開始聯絡上以後,所有他要尋找的故人,找到人後,又要存問迴護,這些要聯繫的事,都是由書信往返。到了八九年底,懷師派了他的三位學生,李省吾、賈寧、尹衍樑博士等到成都,遍請維摩精舍諸位老宿以及賈題韜先生等人,代表懷師的問候。他們也到過灌縣靈巖寺,當年懷師與袁大老師因緣會遇的地方,也是懷師最懷念的地方。尤其在靈巖寺靈泉石壁上所刻的兩句話「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懷師還為它特別請人製成一顆長方的印章,做為圖記。他們三位臨去的時候,由李省吾留下了兩萬美金,後來還從臺灣寄來一部新文豐出版社印出的一部大藏經,「龍藏」給成都維摩精舍的諸老,做弘法及廣結法緣之用,結果都由賈題韜老先生自行處理了。接著有李淑君小姐來過成都,她也是懷師的學生,也是代表懷師來訪問的。
到了一九九○年的三月,懷師又派出家的弟子,宏忍、親證二位法師(尼師)來成都,帶來美金二萬伍仟元,希望諸老宿們代表發揚維摩精舍的法緣。他們與李自申老先生、鄧嶽高老先生、楊志堅老先生、袁淑平老師、傅淵希老先生等商議,將此款先存進銀行,後來賈題韜先生從外面回來,別有意見,於是經李、鄧、楊、袁、傅諸老的決議,既不能專款專用,將原款提出匯轉給懷師。他們臨財不茍的風格使我們敬佩不已,從此懷師對成都佛法界的一番心願,暫時擱起,因為他正在發願為浙江修造一條金溫鐵路,事情實在太忙,就無暇及此了。至于賈題韜先生,自己直接與懷師通訊聯絡,并且於一九九○年十月十日,隨廈門南普陀寺的妙湛老和尚到香港面會懷師。其中經過種種我們就不知其詳了。妙老也就是閩南佛學院的主持人,年過八十餘,為當今佛門大德。懷師為南普陀發起修建了一座禪堂,據說出資美金四十萬元,是由郭姮宴、李省吾、李真吾三位所發心供養的。我們曾在信上問過懷師有關禪堂的事,懷師回信只簡單的說「禪堂易建,僧寶難求」,又說只恐是「禪堂有住,心無住,那就會辜負西來一瓣香」。但有了一個禪堂也好,總可少被外國人笑我們「大唐國內無禪」吧!
在這段時期中,據懷師那裡來過成都的學生們提起,賈題韜先生曾有信勸懷師出來做「馬丁路德」,為振興中國佛法努力,而且在香港當面也提出這個問題。賈說:有世出世間的學問,無真修實證過來不行;有修持的但無世出世間的學問不行;又有學問又是真修實證過來,而且更有一層是別人所缺少的,你還是一個陶朱公呢!懷師卻一笑而說:賈先生真想把我推到火爐上去烤呢!我既無修為又無學問,而且是一個假陶朱,那有真材實料。於是他又引用了一首張船山的詩來形容自己,引用之妙,又非常的恰當可愛。
爐火焙香靜自焚 維摩一室斷聲聞
到門賓刺如紅葉 過手家財是白雲
食少衹堪分鶴料 心空無礙入鷗群
儘將書籍零星賣 遮眼唯留梵篋文
賓刺就是來拜訪客人的名片,多到有熱情如火的紅葉一樣紛紛重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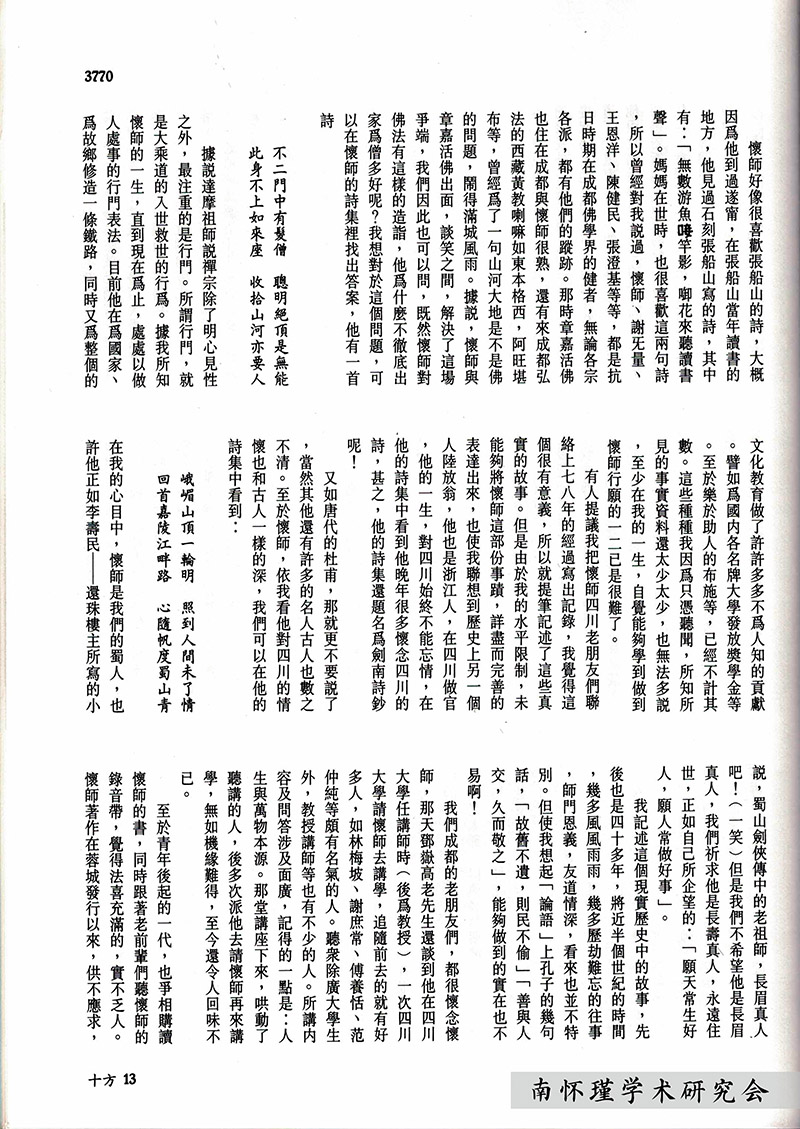
懷師好像很喜歡張船山的詩,大概因為他到過遂甯,在張船山當年讀書的地方,他見過石刻張船山寫的詩,其中有:「無數游魚唼竿影,啣花來聽讀書聲」。媽媽在世時,也很喜歡這兩句詩,所以曾經對我說過,懷師、謝無量、王恩洋、陳健民、張澄基等等,都是抗日時期在成都佛學界的健者,無論各宗各派,都有他們的蹤跡。那時章嘉活佛也住在成都與懷師很熟,還有來成都弘法的西藏黃教喇嘛如東本格西,阿旺堪布等,曾經為了一句山河大地是不是佛的問題,鬧得滿城風雨。據說,懷師與章嘉活佛出面,談笑之間,解決了這場爭端,我們因此也可以問,既然懷師對佛法有這樣的造詣,他為什麼不徹底出家為僧多好呢?.我想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在懷師的詩集裡找出答案,他有一首詩:
不二門中有髮僧 聰明絕頂是無能
此身不上如來座 收拾山河亦要人
據說達摩祖師說禪宗除了明心見性之外,最注重的是行門。所謂行門,就是大乘道的入世救世的行為。據我所知懷師的一生,直到現在為止,處處以做人處事的行門表法。目前他在為國家、為故鄉修造一條鐵路,同時又為整個的文化教育做了許許多多不為人知的貢獻。譬如為國內各名牌大學發放獎學金等。至於樂於助人的布施等,已經不計其數。這些種種我因為只憑聽聞,所知所見的事實資料還太少太少,也無法多說,至少在我的一生,自覺能夠學到做到懷師行願的一二已是很難了。
有人提議我把懷師四川老朋友們聯絡上七八年的經過寫出記錄,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所以就提筆記述了這些真實的故事。但是由於我的水平限制,未能夠將懷師這部份事蹟,詳盡而完善的表達出來,也使我聯想到歷史上另一個人陸放翁,他也是浙江人,在四川做官,他的一生,對四川始終不能忘情,在他的詩集中看到他晚年很多懷念四川的詩,甚之,他的詩集還題名為《劍南詩鈔》呢!
又如唐代的杜甫,那就更不要說了,當然其他還有許多的名人古人也數之不清。至於懷師,依我看他對四川的情懷也和古人一樣的深,我們可以在他的詩集中看到:
峨嵋山頂一輪明 照到人間未了情
回首嘉陵江畔路 心隨帆度蜀山青
在我的心目中,懷師是我們的蜀人,也許他正如李壽民 — 還珠樓主所寫的小說,蜀山劍俠傳中的老祖師,長眉真人吧!(一笑)但是我們不希望他是長眉真人,我們祈求他是長壽真人,永遠住世,正如自己所企望的:「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做好事」。
我記述這個現實歷史中的故事,先後也是四十多年,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幾多風風雨雨,幾多歷劫難忘的往事,師門恩義,友道情深,看來也并不特別。但使我想起《論語》上孔子的幾句話,「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能夠做到的實在也不易啊!
我們成都的老朋友們,都很懷念懷師,那天鄧嶽高老先生還談到他在四川大學任講師時(後為教授),一次四川大學請懷師去講學,追隨前去的就有好多人,如林梅坡、謝庶常、傅養恬、范仲純等頗有名氣的人。聽眾除廣大學生外,教授講師等也有不少的人。所講內容及問答涉及面廣,記得的一點是:人生與萬物本源。那堂講座下來,哄動了聽講的人,後多次派他去請懷師再來講學,無如機緣難得,至今還令人回味不已。
至於青年後起的一代,也爭相購讀懷師的書,同時跟著老前輩們聽懷師的錄音帶,覺得法喜充滿的,實不乏人。懷師著作在蓉城發行以來,供不應求,有兩次在書店遇上出售懷師的書,身上錢未帶夠,拿錢再去就已銷售一空。目前懷師著作在蓉城各大書店大量供應,暢銷得很。據悉還有一些書店,直接找到老古文化出版社劉雨虹先生,想要大量自行出版銷售懷師的書。懷師的著作、思想必將成為五千年東方人文文化新的里程碑,必將弘揚於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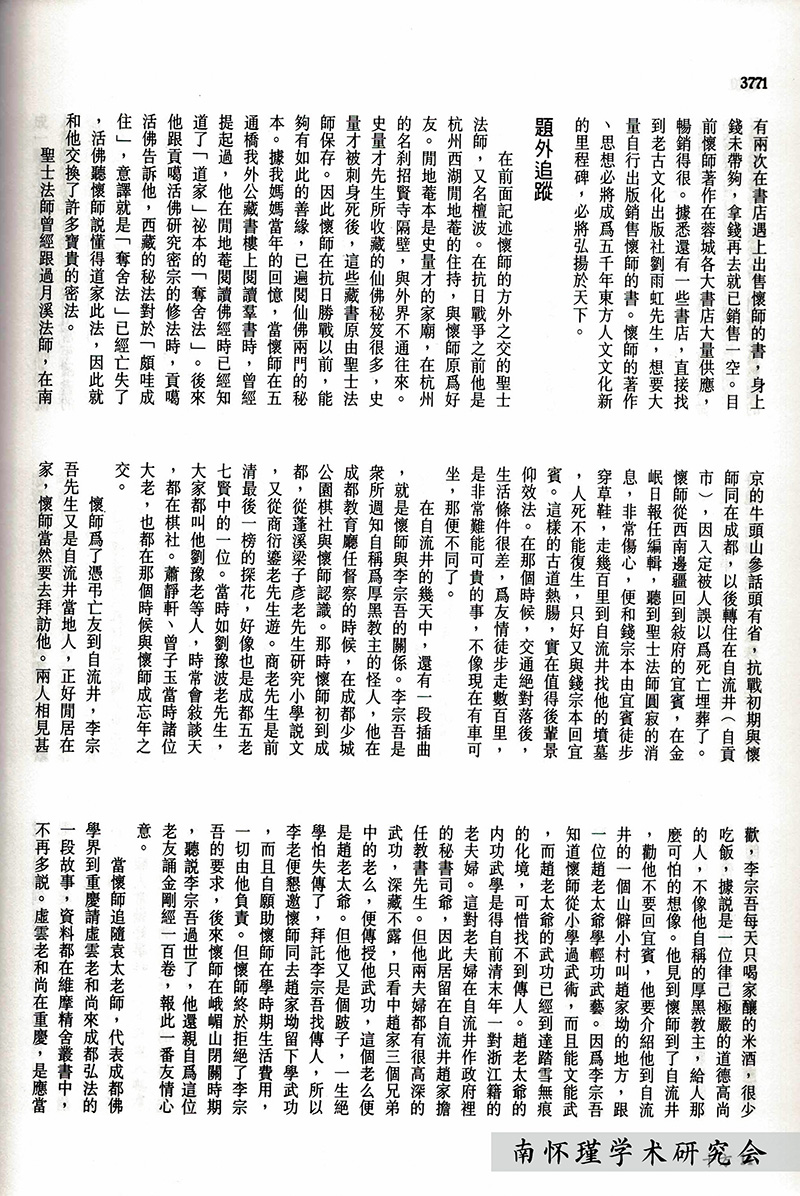
題外追蹤
在前面記述懷師的方外之交的聖士法師,又名檀波。在抗日戰爭之前他是杭州西湖閒地菴的住持,與懷師原為好友。閒地菴本是史量才的家廟,在杭州的名剎招賢寺隔壁,與外界不通往來。史量才先生所收藏的仙佛秘笈很多,史量才被刺身死後,這些藏書原由聖士法師保存。因此懷師在抗日勝戰以前,能夠有如此的善緣,已遍閱仙佛兩門的秘本。據我媽媽當年的回憶,當懷師在五通橋我外公藏書樓上閱讀群書時,曾經提起過,他在閒地菴閱讀佛經時已經知道了「道家」祕本的「奪舍法」。後來他跟貢噶活佛研究密宗的修法時,貢噶活佛告訴他,西藏的秘法對于「頗哇成就」,意譯就是「奪舍法」已經亡失了,活佛聽懷師說懂得道家此法,因此就和他交換了許多寶貴的密法。
聖士法師曾經跟過月溪法師,在南京的牛頭山參話頭有省,抗戰初期與懷師同在成都,以後轉住在自流井(自貢市),因入定被人誤以為死亡埋葬了。懷師從西南邊疆回到敘府的宜賓,在金岷日報任編輯,聽到聖士法師圓寂的消息,非常傷心,便和錢宗本由宜賓徒步穿草鞋,走幾百里到自流井找他的墳墓,人死不能復生,只好又與錢宗本回宜賓。這樣的古道熱腸,實在值得後輩景仰效法。在那個時候,交通絕對落後,生活條件很差,為友情徒步走數百里,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不像現在有車可坐,那便不同了。
在自流井的幾天中,還有一段插曲,就是懷師與李宗吾的關係。李宗吾是眾所週知自稱為厚黑教主的怪人,他在成都教育廳任督察的時候,在成都少城公園棋社與懷師認識。那時懷師初到成都,從蓬溪梁子彥老先生研究小學說文,又從商衍鎏老先生遊。商老先生是前清最後一榜的探花,好像也是成都五老七賢中的一位。當時如劉豫波老先生,大家都叫他劉豫老等人,時常會敘談天,都在棋社。蕭靜軒、曾子玉當時諸位大老,也都在那個時候與懷師成忘年之交。
懷師為了憑弔亡友到自流井,李宗吾先生又是自流井當地人,正好閒居在家,懷師當然要去拜訪他。兩人相見甚歡,李宗吾每天只喝家釀的米酒,很少吃飯,據說是一位律己極嚴道德高尚的人,不像他自稱的厚黑教主,給人那麼可怕的想像。他見到懷師到了自流井,勸他不要回宜賓,他要介紹他到自流井的一個山僻小村叫趙家坳的地方,跟一位趙老大爺學輕功武藝。因為李宗吾知道懷師從小學過武術,而且能文能武,而趙老太爺的武功已經到達踏雪無痕的化境,可惜找不到傳人。趙老大爺的內功武學是得自前清末年一對浙江籍的老夫婦。這對老夫婦在自流井作政府裡的秘書司爺,因此居留在自流井趙家擔任教書先生。但他兩夫婦都有很高深的武功,深藏不露,只看中趙家三個兄弟中的老么,便傳授他武功,這個老么便是趙老太爺。但他又是個跛子,一生絕學怕失傳了,拜託李宗吾找傳人,所以李老便懇邀懷師同去趙家坳留下學武功,而且自願助懷師在學時期生活費用,一切由他負責。但懷師終於拒絕了李宗吾的要求,後來懷師在峨嵋山閉關時期,聽說李宗吾過世了,他還親自為這位老友誦金剛經一百卷,報此一番友情心意。
當懷師追隨袁太老師,代表成都佛學界到重慶請虛雲老和尚來成都弘法的一段故事,資料都在《維摩精舍叢書》中,不再多說。虛雲老和尚在重慶,是應當時國家主席林森字子超,與考試院長戴傳賢之邀請,在重慶做護國息災法會。顯壇由虛老主持,密壇由貢噶活佛主持,這是為了對付日本人正在請高野山的密宗僧人修降伏法來壓伏中國的。懷師與虛雲老和尚結上很深的因緣就在此時。後來懷師隨袁太老師回潼南玉溪口過年,轉返成都以後,他又去過江津,拜訪在江津辦支那內學院講佛學的歐陽竟無大師。那個時候陳獨秀也隱居在江津,與歐陽竟無先生研探佛學,他們談論些什麼,就不得而知了。

懷師峨嵋下山轉到五通橋多寶寺閉關時,路過嘉定(樂山)烏尤寺。那時一代大儒馬一浮先生正在寺中辦復性書院。馬一浮先生是浙江的名宿,據說禪學、道學都很高深,名重一時,但與歐陽竟無先生又各有不同。當懷師請人通報馬先生特來參訪的時候,馬先生便告訴來人,請懷師在外稍坐,過了一會馬先生命人打開復性書院的大門恭請懷師相見。就是這一做作,把懷師一肚子要問他的問題都縮回去了。懷師後來對我媽媽說,馬先生大開中門迎接,那個舉動就是禪宗的機鋒吧!結果兩個人只敘說了一番鄉情,談了一下峨嵋山閒話。中間懷師曾經提出,聽說馬先生在著作中說「靈光獨耀、迥脫根塵是果位上事」有嗎?馬先生立即答覆那是當年的著作,現在看來統統是葛籐語言,我很想把從前的著作燒了。懷師一聽,立即起座頂禮說:先生言重了,是我多嘴胡鬧。就此告辭退出,馬先生親自送到大門,互相作禮而別。
懷師在峨嵋山大坪寺閉關三年之中,國家主席林子超先生經常來洪椿坪小住。洪椿坪那時留有一問清靜房間,是專為主席住的。每天無事的時候,林主席便幫忙和尚擦香爐,林主席偶然也上大坪寺,但因山高路險,到底腳力不行,又常常半途而返。山下住有一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警衛兵,因為故宮博物院的所有故物,為避日本敵機的轟炸藏在此地。警衛連的兵大多是江浙一帶的人,連長是後來通遠法師的好友,又是老同事,彼此又是同鄉,所以這些外緣便成了懷師三年閉關中的無形護法。當時山中和尚們傳說,峨嵋山有位閉關的師父是大官出身悟道出家的,林主席也常常去拜訪他,這些消息便是這樣來的。
抗日戰爭勝利後,國共合作破裂,國事和川中人事紛紛擾擾。懷師在四川大學演講以後,川大哲學系主任傅養恬,中央軍校教官留蘇出身的葉道信,好像還有一位沈天澤,在報上發表和過毛澤東沁園春的詞,因此被蔣校長免職了。他們都是懷師的好友,連同許多學者知識份子都想紛紛起來組黨,這個時期也正是國民黨第一屆大會開始的時候,許多關心國事的人,認為另組新黨參與國事正是時候,傅養恬、葉道信都以私人身份在成都西門外茶館裡開講座,對平民階級、勞動群眾,講中國文化的精義。傅養恬講大學中庸,葉道信講社會革命,非常熱鬧叫座。但他們幾位卻對懷師提出建議,要懷師擔任組織一個新黨的黨魁。大家認為懷師年輕有為,而且具備世間出世間的學識修養。懷師聽了哈哈大笑說:你們大家是我的好朋友,真想把我抬到火爐上去烤啊!這也是促成懷師趕緊離開成都,先到昆明再回浙江的催命符。
現在賈題韜老先生,又希望懷師出來做中國佛教的「馬丁路德」,懷師答覆他不可能上火爐被烤。現在舊事重提,先後一相對照,默想懷師的一生是多姿多彩嗎?還是多愁多難呢?真也難下定論哩!總之依我看來,懷師的一生,應是一個苦行僧,他的苦行是很難被人所理解的。
總之,懷師一直為了繼承發展弘揚中華五千年來的燦爛文化,作了不懈的努力追求,并有了巨大的貢獻,堪稱是:
業蹟留天地 佛壇一偉人
copyright © 2016-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苏州市吴江区南怀瑾学术研究会
苏ICP备2022019425号-1 苏公网安备3205090210231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