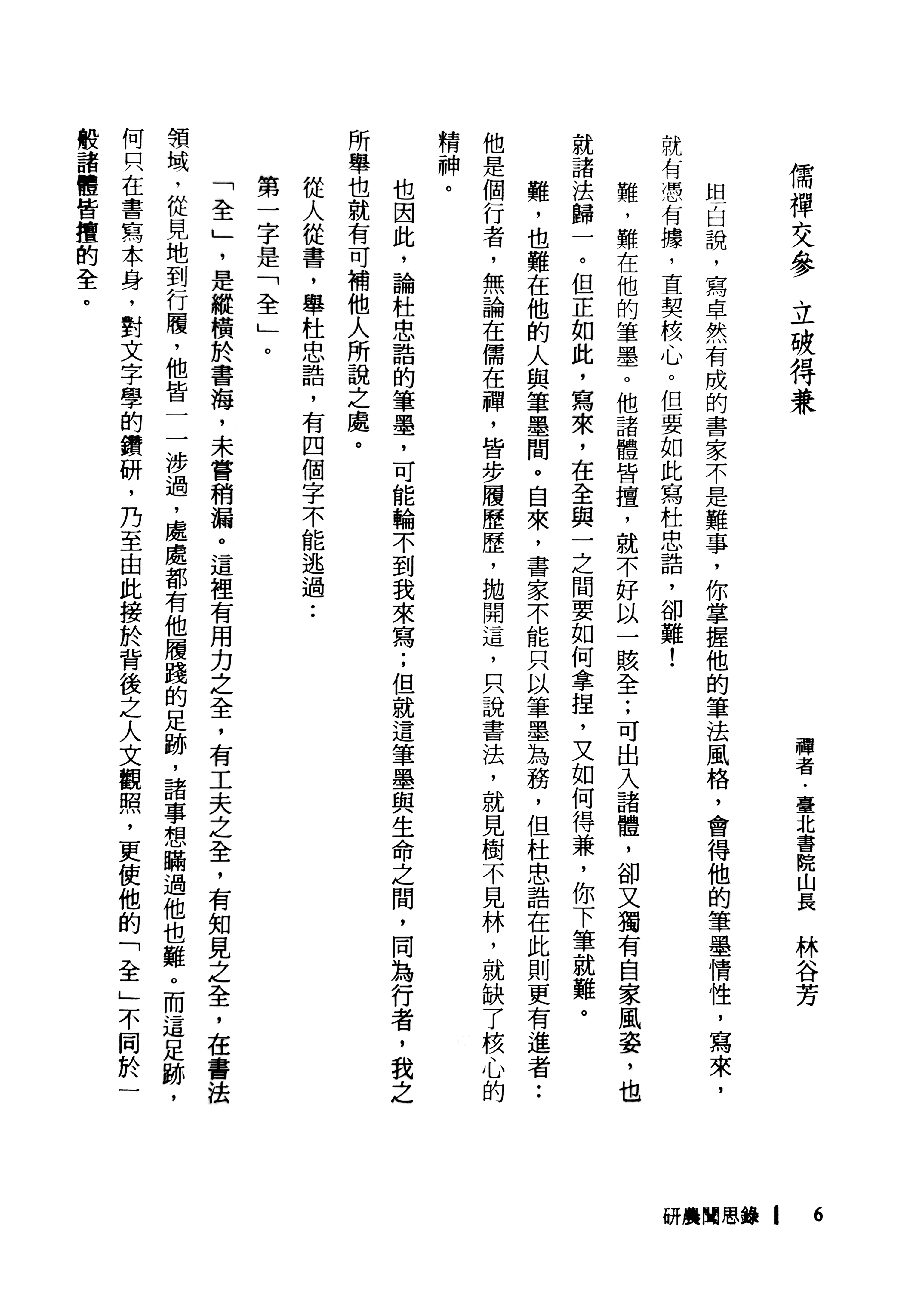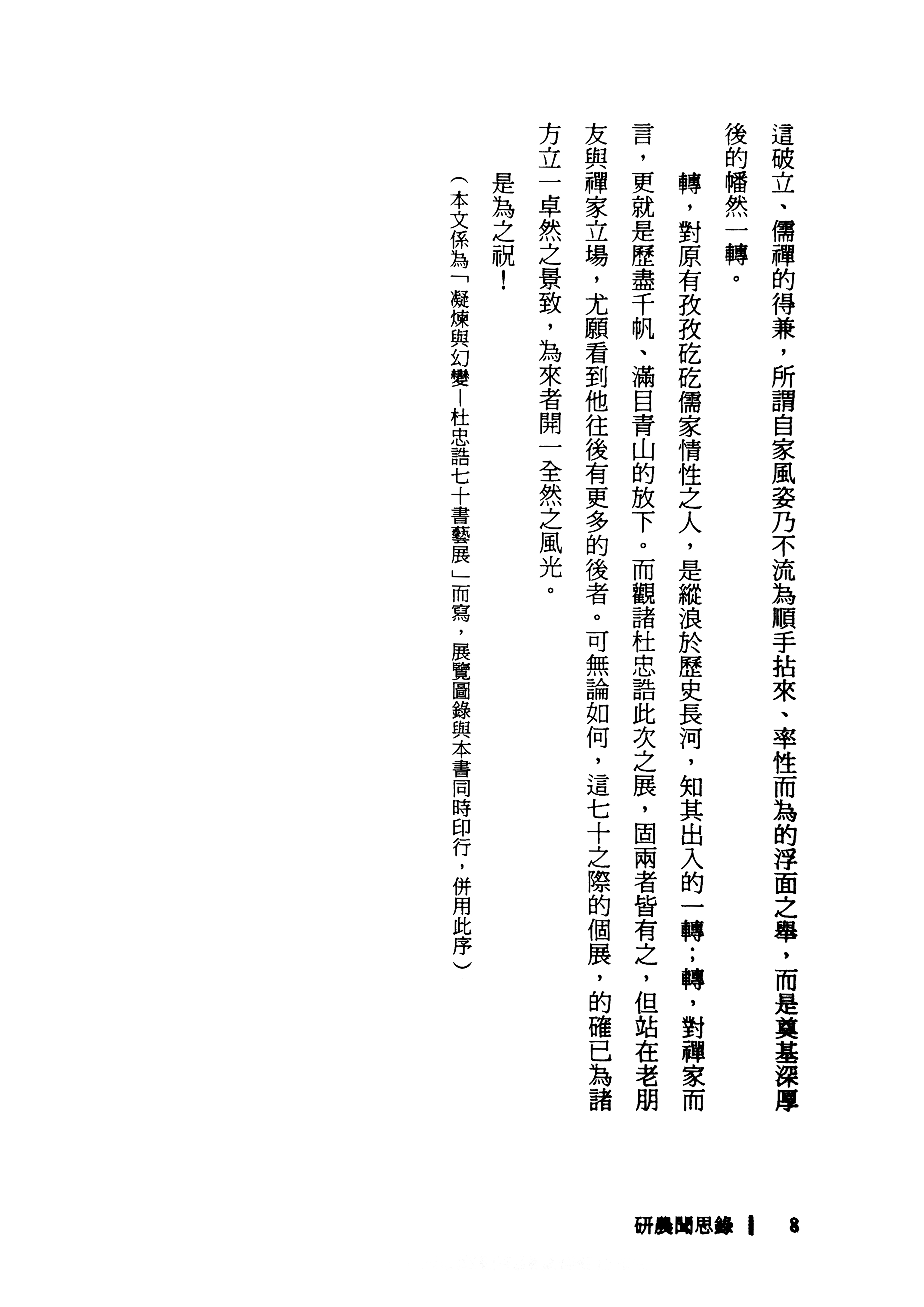儒禪交參 立破得兼
——杜忠誥著《研農聞思錄》序言
禪者 · 臺北書院山長
林谷芳
坦白說,寫卓然有成的書家不是難事,你掌握他的筆法風格,會得他的筆墨情性,寫來,就有憑有據,直契核心。但要如此寫杜忠誥,卻難!
難,難在他的筆墨。他諸體皆擅,就不好以一賅全;可出入諸體,卻又獨有自家風姿,也就諸法歸一。但正如此,寫來,在全與一之間要如何拿捏,又如何得兼,你下筆就難。
難,也難在他的人與筆墨間。自來,書家不能只以筆墨為務,但杜忠誥在此則更有進者:他是個行者,無論在儒在禪,皆步履歷歷,拋開這,只說書法,就見樹不見林,就缺了核心的精神。
也因此,論杜忠誥的筆墨,可能輪不到我來寫;但就這筆墨與生命之間,同為行者,我之所舉也就有可補他人所說之處。
「全」,是縱橫於書海,未嘗稍漏。這裡有用力之全,有工夫之全,有知見之全,在書法領域,從見地到行履,他皆一一涉過,處處都有他履踐的足跡,諸事想瞞過他也難。而這足跡,何只在書寫本身,對文字學的鑽研,乃至由此接於背後之人文觀照,更使他的「全」不同於一般諸體皆擅的全。
破,是超越於既往,未嘗稍歇。有全而未破,就是繼承家當卻不知經營,終成死貨。這破,何只是在諸體間出入;這破,還越過諸體而自成格局;甚且,在年將七旬之際,猶探索出格之可能。而在此,從他卓然有成後仍留學東瀛,就可看出這「打得出」的膽識。
這「全」與「破」,是就他書法的總體樣貌而談,但真談,還得看到在這背後與他生命情性、生命踐行密切相關的兩個字。
儒,是杜忠誥生命最根本的情性與安頓。佛家有所謂宿世因緣者,在這裡,他正如此。
出身寒微,並無家學,杜忠誥髫齡之年,聽人誦蒙學,竟也就隨記無誤,這只能說他稟性原在。而也因這稟性,他越過出身,有胸懷古今之概。
有此胸懷古今,從書而入,自然不偏廢於一方,自然出入於歷朝,也自然不只就字而寫,更及於歷史人文的咀嚼與觀照。
雖說儒釋道原有其相互涵攝處,但三家各有立處與風姿更不待言。而就此,儒是淑世哲學,談的是世間的「立」;禪,則是打破自身習氣的超越修行,在此,是一切盡掃的「破」。
坦白說,以杜忠誥在儒上的夙世因緣,若只此,生命正有不可承受之重,而就因有了禪,這「儒」、這「全」,才真能成為他生命中活潑潑的資產,不僅不妨害自家風姿之成立,更因這破立、儒禪的得兼,所謂自家風姿乃不流為順手拈來、率性而為的浮面之舉,而是奠基深厚後的幡然一轉。
轉,對原有孜孜矻矻儒家情性之人,是縱浪於歷史長河,知其出入的一轉;轉,對禪家而言,更就是歷盡千帆、滿目青山的放下。而觀諸杜忠誥此次之展,固兩者皆有之,但站在老朋友與禪家立場,尤願看到他往後有更多的後者。可無論如何,這七十之際的個展,的確已為諸方立一卓然之景致,為來者開一全然之風光。
(本文係為「凝煉與幻變——杜忠誥七十書藝展」而寫,展覽圖錄與本書同時印行,併用此序)